《从前小桃园》 小说介绍
《从前小桃园》 四 免费试读
四
过年其实是一种传统的麻醉人的方式,不管平时日子过得怎么样,都争着借此机会忘却烦恼。从三十吃到十五,能耍的耍够,能看的看够,很久不见的人见够,吃年饭、放鞭炮、走人户、换红包、打麻将、看灯会、逛庙会,等一鼓作气把十五的元宵吃下去,一年中最兴奋的时刻也就差不多过去。大毛的事没等他们出手就已宣告结束,一帮犯事的人被重庆某个心软有钱的家长集体保了出来,正月初一弥勒佛生日的那个傍晚,闯祸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回了成都。
商量救人的三个对此并不知情,初二晌午华生约了蒋少虎去商业场毛肚店听书良讲情况。华生前脚离开小桃园,后脚冯大毛就进了院子,在向三姨爹三姨妈请安拜年之后,他按纪婉香的线报快步前往毛肚店,去会自己的同党。
商业场那家毛肚老店的生意不错,老板面善和气、火锅色香味浓,灯光柔和不似鸡毛小店惨白雪亮;一间大屋摆着四五张矮方桌,方桌中央跺着小火炉,炉上放着铜锅,桌子周围配着高高的独凳,客人们就坐于高凳上舒舒服服摆弄作坊一样的碗碟、调料和菜肴:毛肚、黄喉、把、脑花、苕粉、豆芽、蒜苗、藕、鸭血、莴笋、菜头、黄鳝、泥鳅、洋芋、香菜、筒筒白。
过年客人不多,蒋少虎坐在桌边招呼上油碟,书良相向而坐正在给自己和华生兑作料,华生刚回头对着掌柜的喊了声:“掺三碗茶。”这时店门口传来一个浑厚压抑着兴奋的声音:“四碗。”他们面前已经站着一位高大结实,留平头,衬衫西裤套棉袄的年轻人。
书良噌的站了起来:“大毛哥哥!”
蒋少虎握着筷子看看来人,咳嗽着用手指着锅对店小二喊:“生火。”华生起身和走近的人互锤了一拳,“这么快就回来了,情绪那么饱满,看来还可以再多关两天。”
大毛边脱外套边挨着他坐了下来,“关起来的时候想的都是你们,你们几个想不想我?”他伸手去搓蒋少虎的头,蒋少虎用手一挡,“想死人家了,还说去救你。”小伙计飞快过来点火、放锅、上油碟,四人也不客气,拿起递上的生鸡蛋敲开,打入油碟,再放上香菜、盐,筷子一搅准备烫菜。
小菜上桌的时候大毛兴致勃勃给大家讲经过。去重庆根本不是探望什么长官,是跟了重庆籍的同学去那边耍几天,那个同学带他去舞厅会几个军校同学,一帮人中有两个男生正在为一个女生勾心斗角,仇人相见分外眼红,说得不合就动起手来,众人开始两边劝架,劝着劝着就打了起来,结果集体被抓到警察局靠墙壁。
“在警察局就握手言欢了,还没去前线自己人先动起了手,也不敢招认真实身份,宁可被当成混混处理,尴尬得很哪!”大毛把棉袄披在肩膀上,配上高大结实的身材,非常张扬中央航校的气质。
华生笑了起来,“打了人都是正面形象,绝对的人物。我们还在想办法准备救人,你要再不回来,少虎会第一个冲去重庆救人。”
“此事万万不可让家里晓得,都帮着保密。”大毛领情地端起了茶杯,“以茶代酒敬各位兄弟妹妹,谢了,就数你们关心我。过两天那帮人要来成都活动几天增进下友谊,总共七个,不方便安排在家里,晓不晓得哪儿有合适的旅馆,帮我写两个房间。”
“我给你安排,把时间和人数报来就行。”华生帮忙揽了下来。
大毛一拍他的肩膀,对着其余两个,“看到没有,兄弟!小时候帮他打架没有白打。喂,我走了那么久你们除了想我都有些啥动向,参加***或是加入什么组织没有?”说完用手电筒似的眼光在其余三人脸上晃,“还有,你们有没有发生任何事情,任何?”
大家乖乖地相互看看摇头,书良和蒋少虎抢着开始发言。
惯常的聚会大毛爱谈人生理想或是时事大事,书良爱说学校趣事或自己的小情绪,华生一般不起话题,习惯是支着手当他们的听众,蒋少虎啥事都能插嘴,四个人当中数他的钱包从小到大最鼓,如果轮到他起头,一定离不开吃喝玩乐这档子钱包推动大脑的闲事。
蒋少虎讲了一个关于淘宝的新鲜事情,说商业场二仙茶楼的马昆山搞了个掏江公司,准备抽干望江公园外围河段的河水,挖三百年前在河里埋的一批宝贝,挖出宝贝就献给政府作抗战资金。
“我寡闻了,啥宝贝这么凶险?”大毛对此颇感兴趣。
“成都人都晓得,‘石牛对石鼓,黄金万万五,谁人识得破,买到成都府’,说是明朝年间有人在河中央埋了一大笔金银财宝。”书良抢过了话头,蒋少虎凑过去替她补充,“是明朝张献忠。”
书良白了他一眼,“有人在河中间埋下了财宝,跟着又把工匠们都杀了,想以后回来取宝,结果人没回得来而财宝一直埋在河底不见天日。其中一个工匠装死躲过,把秘密告诉了后人,听说是一大笔奇珍异宝,金银、宝石、玉器,哪个要是挖到了基本可以买下整个成都。”她说到此处打住,把话传给华生,“报上咋说的,你来讲。”
“其实也不是啥新闻,都吵了好多年,说当初张献忠兵败离开成都的时候把搜刮来的巨额财宝藏了起来,江口沉银,这个江口指的哪里谁都不清楚,于是这么些年来凡是江口的河段或多或少都遭各路人马挖了,这次推测江口在望江楼附近。”华生看着蒋少虎,“马昆山是你们商业场的,他的事情你该更清楚,你说说看。”蒋少虎耸了耸肩膀,“晓得的不比你多,这种事情人家不愿多透露的,反正马昆山手头银两充足,听说又掌握有确凿藏宝资料还有政府撑腰,志在必得,正在组织人马和机器,等枯水季节一到就抽水开挖,人家敢公开说如果挖出宝贝会向政府捐赠作抗战资金,名利双收的事情。”
大毛手摸下巴,“原来传说有这么大的魅力,政府想整治河道的话就多发布这种江口沉银的消息。不过话说回来,要是能挖出东西倒是件好事,仗要打下去肯定需要大量的资金,要不要一起去挖挖看。”他嘿嘿地笑了起来。
蒋少虎当了真,“要得嘛。”他神秘兮兮凑向其余三人,“我都分析过了,东西不一定藏在河底,说不定是在江口对应的某处岸上。石牛对石鼓,依我看是指向岸边的某个庙子,不是庙子里头就是庙子外头,再不就是看庙前门石兽对着的某棵树子。你们想,河中挖宝都那么费劲,那要真埋还不全城皆知。所以,不在河头,在岸上。”
“这个推断新颖。”华生卫护起他来,“不过我倒是好奇这句藏宝顺口溜是谁编出来的。想想看,要是道听途说瞎猜乱编,该内容毫无意义,而要是知道底细的人所编,他为什么要编这个东西?既然晓得藏有这么一大笔宝贝,反而编一个顺口溜到处去传,好像不太符合情理。”
“永远的军师级人物,难怪小时候都听你的指挥。对头,消息多半是张献忠的人散布的,以假乱真哄人乱找。”大毛干脆地得出了总结,“少虎的推测很有想象力,就是缺了推不翻的依据。”
“要啥依据?我是在排除不合理的说法。在河头埋东西,还石牛对石鼓,绝对搞得全城皆知,不可能。”
“如果是你藏宝肯定全城皆知,别人倒不一定。”书良无不嘲讽。
“你太小看我了,不信的话我藏一个东西你来找,找到算你的,要不要试一下?”蒋少虎不服气地发招。
“你各人去埋,我才难得去找。”两人扯一句还一句地争了起来。大毛搂着华生的肩膀看他们争,笑得像九岁时候一样的灿烂。
“好了不闹了,不谈人家藏的宝贝,安心吃自己的火锅。”华生替斗嘴的双方夹了菜,那两位方才高高兴兴地埋头吃饭。席间书良起身去了店外,想买街边的烤红苕当零食,蒋少虎自告奋勇追着出去帮着付钱。
“哎,回成都真是好啊,可以丢开脑袋里的很多东西,光坐在这儿听故事,甚至看他们两个斗嘴都是一场享受。”大毛将双手抱在脑后,身体朝后一仰,舒服地晃起双腿,“就像是回了小时候,生活没有真正开始也就没有真正的烦恼,入世不深相对的美好。”
“咋呢,起烦恼了?”华生问他。
“不至于,就感慨两句。”
“还没问你呢,毕业回来有啥打算?”
“嗯,有些小打算”。
“要去队伍上?”
“找时间慢慢摆,话长。”大毛拿上筷子夹了一口菜塞到嘴里,把话岔开,“你呢,有啥新动向?”他看看华生,又看看店外。
“你指啥动向?”
“刚才有人可是只给你烫菜夹菜。”
“又在说笑。”
“咋呢,没有的事?”
“没有。”
大毛眨了眨眼睛,怀疑起自己的判断,“好吧,那是我想偏了。吃饭吃饭。”
从初一开始气温就冷得让人不想离开火盆,到了初三晚上放在门外喂猫的水碗里结了冰块,转到白天,居然飞起了少见的毛毛细雪,淡淡地飘在天空,像是有人耐烦地蹲在天上往下洒食用盐。雪落到地上没有化开形成粉末状铺着,把城市改了一个颜色。
华生按承诺去帮大毛物色旅馆。近来市区内的旅馆客满,自从仗打起来以来,来成都逃难躲灾、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,有些常客包住在旅馆十天半个月不走,过年都不例外。好不容易在北新街和九龙巷找到两间合适的床位,价格还算公道。
同学们如约到达,大家先在旅馆做了登记,然后臃肿地踏着潮湿的路面集体去华兴街吃蛋炒饭。席间新老朋友说了很多豪情万丈的话,最后勾肩搭背回各自的住处歇息,大毛让他帮着送九龙巷的几个。
华生领着同学们经中山公园中山公园:1951年改名劳动人民文化宫。向旅馆走去。夜色冷风中公园门前空无一人,远处几个人影晃荡一下隐入了旁边一条蜿蜒后伸的小街。那条街叫作三桂前街,深处有很多做“人肉”生意的地方,烟花柳巷、灯影暗淡,一单单生意趁黑在暗中进行,敢往那边走的大致都是自甘堕落或不怕堕落的人,规矩些的都不走那一方,怕沾上晦气更怕被熟人看到。对于和道德沾边的事情、地方,大家历来敏感谨慎,有些错误可以犯,而有些错误犯了会在家里家外抬不起头。
他们过街去了对面。
到达九龙巷,进了旅店半掩的大门,顺黑暗的通道往前几步便站在了登记窗口昏暗的灯光下。天井中漱夜嘴的老板抬头看了一眼,擦着嘴巴回登记室取钥匙,领着他们去了客房。房间还算干净,四张小床分别靠在两侧墙壁,如果躺在上面不发出鼾声的话,不会有任何的影响。老板领着看了老虎灶取开水的地方,指了茅房的位置,匆匆退下。不久,门口出现一位穿花棉袄花棉裤的女子,额前的刘海一看就是火钳夹出来的效果,一个经济不宽裕却喜欢打扮的人,身上唯一奢侈点的是那股说不清是肥皂水还是驱蚊水的味道。这是干什么的,华生不用多猜已基本了然。女子靠在门框上,搓着冻红的手问大家:“先生些,想不想找人摆龙门阵嘛,或是坐下来打几圈小麻将?”
男同学们没见过这种阵势,你看我、我看你,不晓得如何应对。女子向着身后喊了声:“碧玉,搞快些。”随着一阵轻轻的脚步声,她的同伴出现在房门口。
那是一位着杂色棉衣棉裤秀发齐肩的姑娘,慢慢地走过来站在那儿,对着大家。在她出现的前一秒华生就已莫名的心跳加快,而在和她目光相遇的瞬间他几乎失去了呼吸,盯着面前的那张脸,脑子里瞬间飘满雪花。
是她,裁缝店消失的那位姑娘。
姑娘的刘海梳了起来,用小卡子别住露出了光洁的额头,显得特别安静,犹如夜风中开放的一朵野花。和同伴比起来,同样的花衣花裤,前者土俗她则是绝美,一瞬间华生只觉得心口脑子同时被轻轻一击。姑娘显然也认出了屋子中间站的人,有些拿不定主意是跨进来还是退出去,她的姐妹还在靠门框,靠完左边靠右边。
对于可能的再次相遇,他曾经设想过一些情景对白,比如相遇在书店,就说“你也来买书啊”;在街上,说“你也在逛街”;在电影院,就说“你也喜欢看电影”。目前的状况是完全没料到的那种,什么话也说不出来,都过了好几秒,才听见自己喉咙里的声音:“你跟我来一下。”然后顾不得几个同学傻子一样的眼光,头也不回地出了房间。此种情况此般地离开肯定是需要勇气的,他晓得自己周身的勇气来自于这段时间对她的想念。他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,便在天井停下来等着。
姑娘跟上来迟疑地问了声:“要不要去我那里喝口茶?”
他答:“好的。”
心情好似井里上下浮动的水桶,既有遇见的惊喜又有现实的失落,即使最无边际的猜测也绝猜不到她是如此境况,但是不管该不该去喝这杯茶他都做不到拒绝。姑娘埋头走在前头,领着他顺窄窄的街沿朝旅馆后院走,不时回头提醒:“不要走下面,有青苔。”
她的声音还是那么的好听,碰得人心头叮叮当当作响。他乖乖地跟着,姑娘经过靠外墙的一排简陋矮房子,走到最后的一间,一推门把他让了进去。
这便是她的“家”了。房间很小,只有半个房间的面积,对门另一端有扇打不开的死窗户,只透光不透气,窗外有棵挂着细雪的小树。屋内没有装饰,靠窗矮条桌、靠墙小床小灯柜,外加上床下塞着的箱子等,就是所有的家当。中央地上放着火盆,灰白的炭块仍带火光,屋里十分暖和。姑娘没有管他,自顾自从门后拿了火钳和一个小陶瓷罐走到屋子中间蹲下,往里加了新的孵炭儿孵炭儿:木柴经彻底高温燃烧后冷却形成的炭块,易燃无烟。,待热度起来才回身去条桌上倒茶水。
“你叫碧玉?”他用这句恰当的话开了头。四周没有可以供人坐的凳子,他坐到了床沿,“名字很好听,很配你。”他还是个清白男子,对床的用途没有多想。
“有啥好听的,小家子气,小家碧玉。”姑娘客气着递过来一杯热茶,他笨笨地起身,不想头撞上了床的蚊帐杆;一乱,水又洒出来烫了手;赶忙坐下,脚却不小心踢到了床下的盆子,他的紧张惹得碧玉扑哧笑出了声。
“不,不,碧玉,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”他吟着诗,掩饰起尴尬。
“这两个字还能作诗?我只晓得它的颜色。”碧玉诚实地看着他,他便估计她没怎么念过书,忙岔开了话题以免有卖弄之嫌,“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。”此话一出口便觉得不妥,那像是在说你不该在此地出现,于是他开始无话找话,“房间很整洁,我是说你很会收拾屋子。”
“房子小,有啥好收拾的。”
“上一次在裁缝店,你走得突然。”他把心头想的说了出来。
碧玉回身靠在了桌边,“你家小妹妹好吗?”
“你还记得。”他闻言自然是窃喜,说明她也没有忘记。
“嗯,你那天围了一条好好看的红围巾。”
他暗暗念着三生有幸,哪怕她记住的只是围巾。
隔壁屋子有了动静,是碧玉的同伴,正放大着失望的声音:“睡觉,莫得搞头。”隔壁房门重重地关上,华生觉得有点滑稽,想象着同学们被吓坏的样子。一个男人在店里找姑娘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胆子,这个胆子不是敢不敢猎奇而是敢不敢堕落,刚才他当着大家的面把人带走,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挑战,今晚有人胆敢走在危险的边缘,这个话题大概可以刺激他们一个晚上。
他埋头喝了一口烫茶。
“天暗了,吃完茶你也该回去了。”碧玉全当没听见外面的动静,“住得不远嘛?”
“不远,住宽巷子,我师父的家。”
“你自己的家呢?”
“我没有自己的家,老家在旺苍,爹妈走得早,八岁一个人流浪来成都,后来跟了师父。”
“有兄弟姐妹没有?”
“曾经有一个弟弟,叫星星,爹妈过世后被亲戚卖了,四岁,找了多年一直没找到。”他不知道为什么想跟她说星星的事,一般他是不愿对外人提起的,一个不想碰的伤疤。碧玉“哦”了一声,拿水瓶替他掺了茶。他怕她以为这个问题让他难过,“你呢,家住得近吗?”
“我家不在成都。”碧玉答得快而干脆,似乎不想谈自己的事,他却想多了解一些,“冒昧问一句,咋过年都不回家?”
“晓得冒昧还问,我都没问你咋不待在师父家而是跑到这里来耍?”碧玉反呛一句,不过口气却十分柔和。他便把同学们来成都的前因后果说给她听,尽量讲得有趣,晓得自己是想调节气氛逗她开心。碧玉果真笑了,“希望他们没有被我老乡吓到。”
“不会,怕是被我吓倒了。”他调侃一句随即正色起来,“你们是老乡?倒是没听出来,她说成都话带卷舌音,你没有。”
“大概我学得快些。”
“你看,我回答了你的问题,现在该你回答了。”
碧玉好脾气地看着他,好像面对的是一个爱问问题的顽童,“你有点好奇哈,好奇心有好有歹,想你也不是坏心。”
“不,是关心。”
她沉默了,“好吧,难得你问,想听的话我讲给你听;不过,讲这些不该喝茶,喝酒好不好?”她从桌上拿起一个茶缸,过来从床下摸出个瓶子倒了大半杯深色的东西,屋子里一下飘起烈酒呛鼻的味道;见华生盯着自己,她笑着将杯子放在嘴边蜻蜓点水似的抿了一口,“不要怕,我不是酒鬼,前阵子崴了手腕,兑的药酒。”华生拿过她手中的酒瓶,去门口倒空了自己的茶杯樽上酒仰头就是一大口,他并不爱喝酒但现在很想喝,不是为了壮胆,是为了寻找一种境界。
碧玉回到条桌边一踮脚坐了上去。他看到了她脚上穿的花棉鞋,成都人称为“抱鸡婆”的那种,那么土气的样式居然被她穿得调皮,突然就有冲动想伸手去摸一摸那两只可爱的脚。
他埋头又喝了一大口,把发热的想法压了下去。
碧玉没有管他,独自坐着望着火盆里的炭火出神。屋里很暗,昏暗的电灯光照着她光洁的脸蛋,她的皮肤是成都姑娘特有的那种没有被太阳晒过的白净,在花衣服的衬托下显得过于苍白。她眼波蒙眬,让人一时难以确定主人的心思。要是面对的是书良不用猜就能八九不离十地知道答案,不管书良想什么你看她的大眼睛就晓得是让人发怒、伤心,还是高兴的事情,但对碧玉他看不透,也许是还不了解,那种表情算迷失还是算安静?但有一点是清楚的,就是她那个样子让他心口有些发痛。他突然觉得此时的好奇是一种怪癖和罪过,大过年的实在不该问这种伤感问题,一个人有家不回当然有原因,而所有的原因追究起来肯定没有一个会是轻松愉快的。
“可不可以收回我的问题,只借一口酒喝?”他改了主意。
“问是你先问,酒喝下去又不想听了?”碧玉抬起了头。
“改天问好不好?”
“好奇和关心那么快就被吓跑了。好,不说了,反正也不是啥好听的事。”她端起杯子一口一口喝了下去,脸蛋很快泛出桃花红。
酒精让神经松弛下来,神经一松弛神思也就四下飘飞。两个人东一句西一句说了一阵,然后收了声,有酒为伴说不说话都不打紧,反正脑子里到处都是独白的声音。华生只觉得浑身发热伸手敞开了外衣领口,酒劲已经上到了脖子,烈酒入口真似一瓢汽油浇到炭上。
火盆里的炭火暗了下去,碧玉从桌子上跳下来,过去往盆子里加了孵炭儿,她没有回到桌子而是走到床边,挨着他坐了下来。他端着酒杯坐得笔直,尽量让自己放松,尽量坦荡。
“好久没有跟人讲过这么多的话了。”她低低地说道。
“想说什么随便就是,我喜欢听。”
窗子外的夜深了,裂开的云层中露出那轮就要圆满的月亮,灰蒙暗淡,罩着地面上一片风吹草动都听得清楚的安静。火盆里的木炭闪着隐约的红光,熄灭的地方堆起了新的灰烬,屋里弥漫开炭块燃烧后的特殊气味,出世离尘的味道。如果不介意炭味和檀香的区别,完全可以闭起眼睛想象这是某个寺庙客堂,然后随着黑夜、烈酒和自己喜欢的人,纠结出一段缠绵。
他从喉咙里冒出一句:“月亮好圆。”
接下去的记忆他几辈子都不想忘记。
碧玉站了起来,从他手中拿走了酒杯,“不要再喝了,会醉的。”他果真就感觉一片醉意,并不知道自己微醉、领口敞开、前额搭着头发的样子有多么可爱。碧玉站在他面前轻轻摸了他的脸,像一个小女孩问小男孩:“你叫啥子名字?”
“赵华生,华西坝的华,生活的生。”他嘴巴发干,不过脑子还算清醒。她的靠拢让他血脉加速,感觉某个时刻要来了,就是曾经期待的,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那种时刻。他笨手笨脚地起立,所有的期待都想靠岸。他伸出手试探着去摸她的脸、她的手臂、她的皮肤……他们靠得那么近,她的体温让他浑身肌肉发软,只有部分相反。
外面街上传来了“咚、咚”两声竹棒子的敲击声,更夫在打二更,进了亥时亥时:晚上九点至十一点。。屋里没人去管那是什么样的信号,只想把周围忘掉,放灵魂自由出窍。
也不晓得过了多久才停了下来,碧玉将他推开一定距离,笑了,把他拉到镜子前,他看见了自己脸上的红印子。碧玉递上一条毛巾,自己则坐到床边,在昏暗的光线中对着床头的小镜子整理头发,一副已经结束的样子。
他的胸口出了汗,身体在悸动中散热回神还想继续。他贴在她身后坐了下来,越过她的肩膀从镜子里去看她的脸,他们的脸都泛着微红,如果不是因为兴奋就是酒劲没散。他看到了自己的眼神,里面燃烧的绝对不是酒精。
碧玉快速从镜子里看了一眼,起身把他拉了起来,“你该回家了,快十点了,当心被师父骂。”她推着他往门口走,他无奈稳住脚,本想再说几句,碧玉二话不多说把他推了出去,推到门外的黑暗地带,就像把一块燃烧的炭火扔到了雪地,然后轻轻关了房门。
四下又冷又静,只有不远的屋子里潜伏着怪兽样的低沉鼾声,即便有月光混着残雪的反射,夜的黑也已全然地嚣张。他呆站了两秒,见碧玉熄了灯,才深吸一口气转身穿过天井院子走到了外面的巷子。一股拂面的冷风让他打了个寒战,巷道内黑黢黢冷飕飕,混杂着阴沟淤泥的腐臭。
他拉拢了衣领,紧走几步上了大街。
街上没有行人,街口的电灯下一个挑担子的夜食摊子不怕冷地在做生意,几个夜不收夜不收:熬夜之人。更是冷不怕的就着昏暗的街灯吃着滚烫的汤圆,其中一个咂着嘴巴喊:再来一碗黑芝麻。一群***完毕的青年男女迎面走了过来,丢盔卸甲地拖着标语旗子,疲惫得不成样子;街边暗处冒出来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叫花子,举着酒瓶子朝***队伍喊:“打倒……坏人……日……”
他没有停下来,加快了步伐朝家赶,即便醉了也不敢忘记小桃园的家规。每晚十点半家里关大门,晚归之人如果没有提前打招呼统统会被关在外面,而任何的晚归不论什么原因都不可以超过敲三更三更:晚上十一点。,否则必遭清算。师父说过:天底下有啥要紧之事非得半夜三更去办?此话看来不假,半夜三更发生的事确实不可言说。
宽巷子中多数的灯还亮着,院落深处传来隐约的人声,他到了自家门前。路灯微光下,门框两侧贴着大姨爹送的眉飞色舞的大红春联:丰衣足食年年乐,国泰民安岁岁兴。他没有看那副眉飞色舞的对联,要是这样的祈福真能送到各家各户,那么他喜欢的人就不会住在那样的巷子过那样的生活。
一抬手推开小门进了院子。
内院里没有灯火,师父师母外出还没有回来。他轻声走到吴妈的窗下放平声音报了平安,然后回了自己的屋子,没有开灯,径直走到床边躺了上去。
风助涨了酒精的后劲,碧玉的脸在面前晃。碧玉,碧玉,一闭眼睛脑子里全都是她的影子,她不仅点亮了他的心脏好像也点燃了他的身体,让脉象中生出一股需要被平定的骚乱,一座想沸腾的火焰山。他翻了身,拿起枕头压住了不肯安分的脑袋;但是,不安分是压不住的,让人不想反抗就缴械投降。他松了腰带,手换了位置。
他喜欢和她在一起,想和她在一起,他要和她在一起,他们在一起,在一起,在一起,在一起,一起……
最后火熄了人也倦了,不管是昏过去还是睡过去,反正是安静了下来。在意识消失之前他想的是:爱情,开始了。
 从前小桃园
从前小桃园
 凌雨薇楚樾
凌雨薇楚樾
 宁熙周少虞
宁熙周少虞
 孟紫杨博瀚
孟紫杨博瀚
 胜天半子
胜天半子
 亲生女儿比不上养子
亲生女儿比不上养子
 老婆的白月光
老婆的白月光
 重生后远离伥鬼闺蜜
重生后远离伥鬼闺蜜
 论光环的重要性
论光环的重要性
 再见,再也不见
再见,再也不见
 江湖:社会线人的摸爬滚打。
江湖:社会线人的摸爬滚打。
 人在六十年代,开局支援北大荒
人在六十年代,开局支援北大荒
 凌雨薇楚樾
凌雨薇楚樾
 宁熙周少虞
宁熙周少虞
 孟紫杨博瀚
孟紫杨博瀚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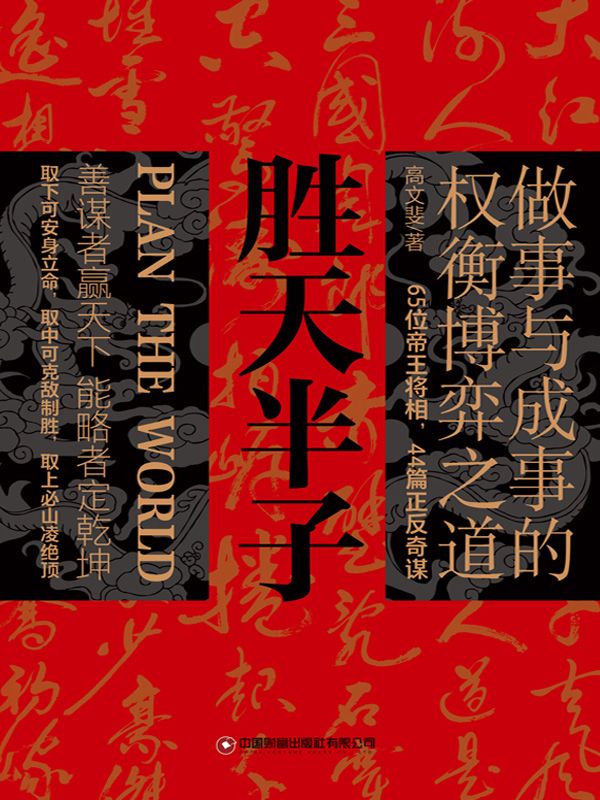 胜天半子
胜天半子
 亲生女儿比不上养子
亲生女儿比不上养子